洗罢砚台回南京
作者:佚名|分类:生活杂谈|浏览:83|发布时间:2025-08-14
收拾文房回金陵
最近整理书籍时,无意中翻出了一块珍藏多年的歙砚。这块砚台是在1998年于安徽西递村购得,当时的摊主是一位操着绍兴口音的老者,至今仍记忆犹新。
当时这方砚台的售价是百元左右,它属于老坑金星石材质,如今市场估价大约为三千元上下。最为独特的是,砚台上天然形成的金色纹理被匠心独运地雕刻成了荷花叶片的形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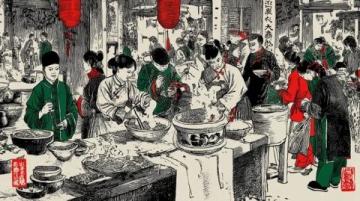
由于一直缺乏合适的砚盒,这块珍贵的砚台从未使用过。后来,一位朋友特意委托匠人定制了一个配套的楠木砚盒。

这个砚盒堪称艺术品,是由整块楠木剖开后精心雕琢而成,工艺之复杂可想而知。
值得一提的是,负责制作砚盒的并非专业的文房用具制造商,而是一位从事家具行业的工匠。这样的委托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个挑战。
当我收到这方砚台和它的专属砚盒时,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实际上,这个精美的楠木砚盒的价值远远超过它所盛放的砚台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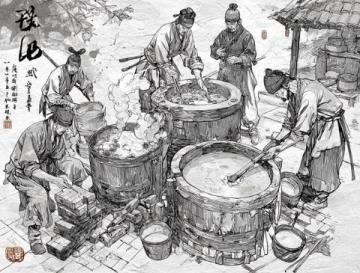
若长久不使用这块珍爱的砚台,实则辜负了为我定制砚盒的朋友的一番心意。
今日返回南京前,特地将砚台清洗干净。倘若砚池内残留墨迹,对砚石不利。

如今砚台的主要用途已转变为储存墨汁而非研磨,而研墨本身则成为了一种奢侈的享受,毕竟耗费的时间成本不容忽视。



记得宋代诗人曾有两句名言:“洗砚鱼吞墨,煮茶鹤避烟。”其中“鹤避烟”较为容易理解,但对“鱼吞墨”的描述却令人费解。个人认为鱼类不会主动摄入墨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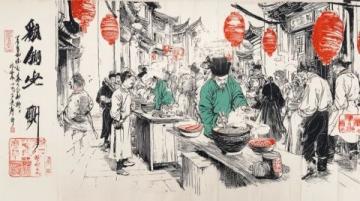
古时流传着一个关于张芝的故事:他临池学书,日久天长,池塘之水皆被染黑。这也是“临池”一词成为书法练习代名词的由来。然而,需明确的是,这并非是池水直接变成墨水的结果;而是书写完毕后将砚台中的余墨倾倒所致。
在王冕的一首诗中提到,“我家洗砚池边树”,这也反映了古人有经常清洗砚台的习惯。
宋代文人常于砚台上刻写铭文,苏轼、黄庭坚等人留下的砚铭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不过这些珍贵的砚石早已散佚无踪。现今一些篆刻家依旧热衷于在砚上雕刻题记,而我的几方砚台却都只是未经雕饰的“光砚”,不免有些惭愧。

关于文房用具的变迁,“移砚”一词曾被用来描述古代文人工作调动时将个人所使用的砚台一同带走的情景。此次我返回南京,也可以称之为一次“移砚”的过程,不过仅是空间上的迁移而已,并未增添太多风雅之意。

附上今日在镇江书写的两幅字以及我的楠木盒砚台的照片。



(责任编辑:佚名)
